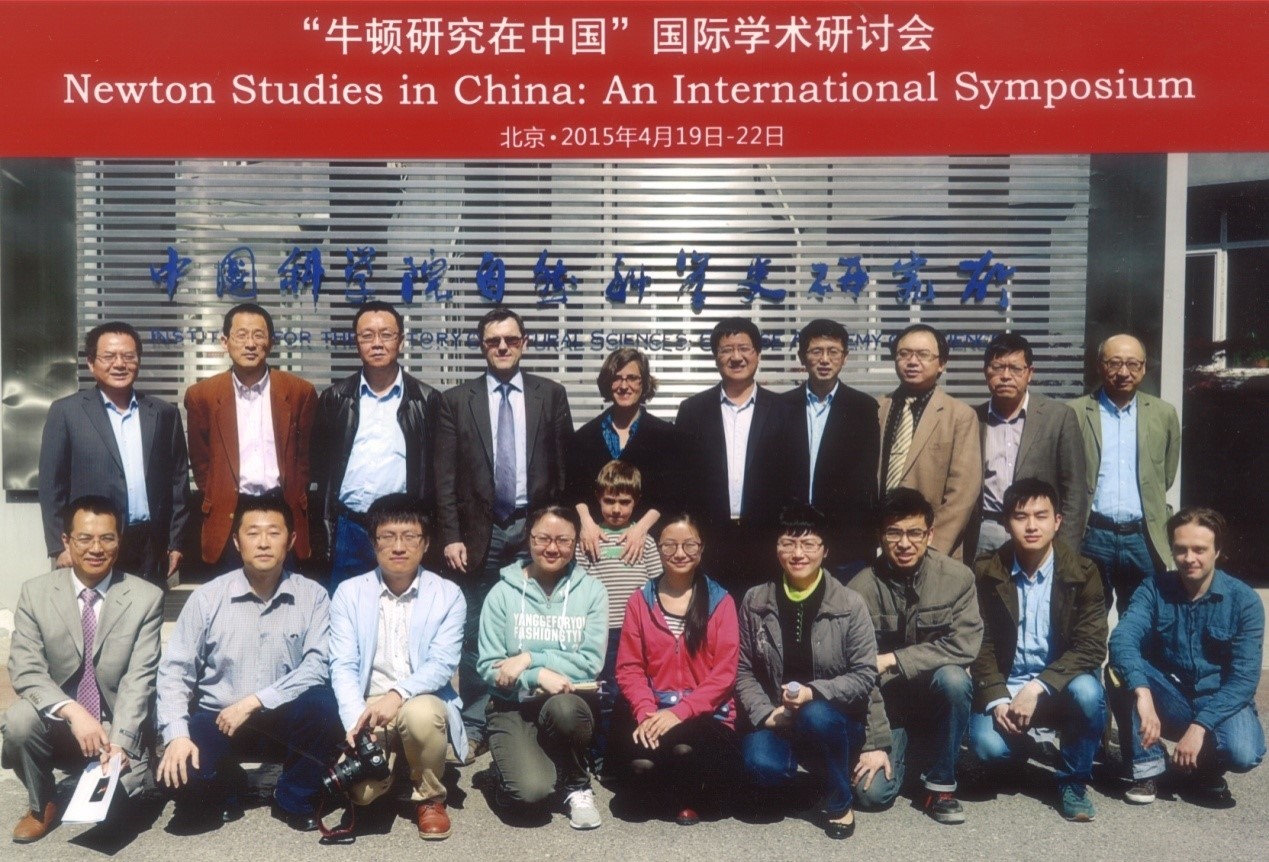应中国科学院大学(国科大)历史系邀请,英国知名科学史学者罗布·艾利夫(Rob Iliffe)教授于2017年9月10日至23日来华讲学。艾利夫现为牛津大学科学史讲席教授,兼任牛津大学科学史、医学史与技术史中心(OCHSMT)主任,《科学年鉴》(Annals of Science)杂志共同主编(2006-)等职。艾利夫教授是目前国际科学史界顶级的牛顿研究专家,长期主持“牛顿项目”(The Newton Project),①且有多部著作问世。
据悉,这是艾利夫教授第二次来华讲学。2015年,他应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邀请,来京参加了“牛顿研究在中国”(Newton Studies in China)国际学术研讨会,与袁江洋研究员共同主持了“中文版《牛顿文集》编辑、翻译与出版”工作坊,其间还在部分高校和研究院所做了牛顿研究系列学术报告。②
此次来访,艾利夫教授主要进行了三方面的学术活动:一是为国科大(雁栖湖校区)研究生开设了“近代科学史”短期课程,二是受邀在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等单位做了多场学术报告,三是参加了牛顿研究前沿座谈会以及《科学文化》期刊第二次编委会。此次讲学活动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有助于深化中英科学史研究者之间的交流,所以本文拟从上述三方面作一综述。
1.“近代科学史”短期课程
艾利夫教授开设的“近代科学史1500-1900”课程共六讲,由六个主题组成。(1)“亚里士多德的哲学”(The Aristotelian Philosophy),对比讲述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即科学),以及亚里士多德主义对基督教科学思想和伊斯兰科学思想长达上千年的影响。到了十七世纪早期,亚里士多德体系才在内在矛盾与新柏拉图主义的共同作用下趋于瓦解。(2)“工具、实验和科学革命”(Instrumentation, Experiment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十七世纪的自然哲学家抛弃了反对利用工具和干预手段来研究自然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转而强调科学方法和科学工具在研究自然过程中的无比重要性。谈到十七世纪最为重要的科学仪器,流行的观点认为是望远镜,艾利夫教授则强调应是显微镜,因为后者为人类开辟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具有深刻的哲学和神学含义。(3)“自然的数学化”(The Mathematization of Nature),主要探讨“自然在本质上是数学的”这一断言的含义,具体涉及开普勒、伽利略和牛顿的工作。(4)“突破地质时间的限度”(Bursting the Limits of Geological Time),主要讨论地质学上的一些理论和发现——正是这些理论和发现促使人们认识到地球和宇宙实际上已经存在几十亿年了,而非原来所认为的四五千年。(5)“进化论与优生学”(Evolution and Eugenics)。该讲首先讨论了基于自然选择的进化论的诞生,然后分析了这一理论如何促生了关于“人种可以通过科学方法得以改良”的讨论,最后则论及优生学二十世纪上半页的实践以及对当今的影响。(6)“热力学的诞生”(The Birth of Thermodynamics),主要讲述十九世纪早期的热能理论,探讨汤姆生等科学家是如何发明热力学第一、第二定律的。通过上述六大主题,艾利夫教授不仅梳理了西方近代科学史的大致轮廓,而且对多个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③
艾利夫教授还为本课程精选了一份“最简”参考书目,建议感兴趣的学生深入阅读。其中一本为概论性著作:P. Bowler and I. Morus, 《现代科学的形成》(Making Modern Science: A Historical Survey, Chicago, 2005)。其余六本则与六次讲座依次配合:(1) D. C. Lindberg, 《西方科学的起源》(The Beginnings of Western Science, 2nd ed., Chicago, 2008),(2)S. Shapin, 《科学革命》(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Chicago, 1996),(3) P. Dear, 《科学的革命化》(Revolutionizing the Sciences, 2nd ed. Chicago, 2009),(4) M. Rudwick, 《突破时间的限度》(Bursting the Limits of Time: The Reconstruction of Geohistory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 Chicago, 2005),(5) A. Desmond and J. R. Moore, 《达尔文的圣业》(Darwin's Sacred Cause, London, 2012),和(6) D. S. L.Cardwell, 《热力学的兴起》(From Watt to Clausius: The Rise of Thermodynamics, New York, 1971)。此外,在接受学生记者采访时,艾利夫教授还推荐了另外两本科学史著作:T. S. Kuhn, 《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2nd ed. Chicago, 1970) 和B. A. Elman, 《科学在中国(1550-1900)》(On Their Own Terms: Science in China, 1550-1900, Cambridge, MA, 2005)。
艾利夫教授全程英文授课他还精心准备了图文并茂的课件,尽量在讲座前一天上传,以便学生及时预习。讲座受到热烈欢迎,每一讲都采取“两小时讲座 + 半小时问答”的形式。在问答环节,学生们提问踊跃例如:如何理解宗教在近代科学家思想中所扮演的角色?作为科学史或科学哲学专业的学生,应该如何看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关系?作为《科学年鉴》杂志主编,可否为中国学生撰写英文论文提供一些建议?……艾利夫教授旁征博引而又不失风趣的回答,经常博来阵阵掌声。
除了开设“近代科学史1500-1900”课程,艾利夫教授还为国科大的研究生做了两场学术报告:一是科学史博士前沿讲座,题目为“牛顿主义与天才观念的变迁”(Newtonianism and Changing Ideas of Genius,9月15日,中关村校区,主持:袁江洋教授);二是明德讲堂,题目为“科学与宗教”(Science and Enlightenment,9月19日,雁栖湖校区,主持:袁江洋教授)。其中明德讲堂听众爆满。
2. 四场学术报告摘要
国科大之外,艾利夫教授还受邀在北京大学医学部、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以及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做了四场学术报告,其中有三场涉及牛顿研究的前沿问题。
达尔文与优生学(Darwin and Eugenics,北京大学医学部,9月18日,主持:张大庆教授)。一旦人们认识到地球历史久远,远超基督徒从《圣经》中得出的年限,进化论便应运而生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受到了多方面的启发。达尔文对拉马克的进化理论、佩利的自然神学、莱尔的地质渐变原理,既有继承也有扬弃。跟随贝格尔号的航行(1831 – 1836)给了达尔文独特的便利条件,使他得以考察各地不同的物种及其化石,从而得出了基于自然选择的生物进化思想。几乎与此同时,华莱士也独立得出了与达尔文类似的理论。不过,华莱士具有浓厚的宗教倾向,认为自然选择机制并不适用于优越的人类,而且进化过程并不是永恒的。达尔文则不然,爱女的夭折驱散了他原本薄弱的宗教情怀,使他更加倾向于相信上帝和灵魂不过是神话。虽然达尔文在《物种起源》(1859)中对人类的进化着笔不多,但是他在《人类的由来》(1871)中讨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人类并不见得优于动物,甚至人类本就源自动物,而物竞天择是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物种生存的永恒法则。达尔文主义逐渐大行其道,其影响很快突破了生物界,被应用到社会领域。达尔文的一位表亲高尔顿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和达尔文的进化论糅合起来,创立了优生学。该学说在二十世纪上半页被一些国家付诸实施,通过绝育、堕胎乃至屠杀的手段来限制某些人群或某类人的繁衍,其中最恶劣的例子便是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暴行。二战以后,虽然优生学一词已成禁忌,但是在人口膨胀压力下,新马尔萨斯主义开始兴起。时至今日,人们已可通过超声检查等现代科学技术,预先诊断胎儿的性别或健康情况,进而通过堕胎等手段防止某一性别或残疾儿童的出生。这种做法虽然没有冠以优生学的名字,但实际上正是当初优生论者梦寐以求的做法。
牛顿思想中的科学与宗教关系(Interactions between Science and Religion in the Thought of Isaac Newton,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9月21日,主持:谢爱华教授)。本次讲座的核心观点,与艾利夫教授2015年4月2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所做的题为“近代早期的科学与宗教关系:两条道路”的讲座一致,即近代西方有两种貌似相反的进程同时左右着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一是科学日益增强的解释世界的能力消减了宗教的权威,科学逐渐被视为启蒙的关键和进步的标志;一是关于人体和宇宙的大量科学发现又强化了自然神学,从而支持了宗教。在这方面,牛顿的《原理》发挥了尤为重要的作用。《原理》一方面可以视为科学和理性的胜利,被启蒙思想家拿来攻击宗教和迷信;另一方面也可视为宗教的胜利,因为它也可用来证明创造者上帝是一位完美的几何大师,从而支持了设计论。正因如此,牛顿的《原理》至今仍是设计论者的理论基石。对于牛顿而言,自然和《圣经》都是同一位上帝的杰作,研究自然与研读《圣经》一样,也是一种宗教行为。不过,牛顿认为研读这两本书需要的特别的努力和恰当的方法,而他自己就是少数蒙选者之一,受命来为人类解读自然的数学密码和《圣经》的预言密码。
牛顿与科学天才概念的产生(Newton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Scientific Genius,清华大学科学史系,9月21日,主持:吴国盛教授)。 在西方传统上,天才最初只与艺术家或作家有关——伟大的艺术家和作家受到某位缪斯女神或基督教的上帝的启发而创作了不朽的篇章。尽管人们也会说某位自然哲学家(科学家)拥有研究某门数学或科学的天分,但是不会将他们与天才联系在一起,因为人们认为上帝乃是自然的真正作者,哲学家不过是发现了早已存在的知识而已。只有到了十八世纪,欧洲思想界才产生了“科学天才”的概念。这一概念的出现,与世俗化倾向、对科学创造性的新颖描述、资产阶级知识产权观念密不可分。随着科学团体中越来越看重方法,随着“受启蒙”的民主化形式的出现,科学天才既被当成一个世俗的圣徒,又被视为智力的翘楚;既被当成一个想象力超群的人,又被视为科学方法的创始者和奉行者。牛顿无疑是最符合这些新条件的一个“天才”。在将牛顿塑造为第一个科学天才的过程中,牛顿的外甥女婿康杜伊特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通过收集、整理牛顿的逸闻趣事,将牛顿描绘成一个平凡而又非凡的世俗圣徒。吊诡的是,一个科学天才被认为是一个拥有非凡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人,但是牛顿本人生前是非常警惕甚至反对想象的。牛顿认为想象是偶像崇拜、情欲和虚构的源头,科学进步依靠的不是个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而是理性、刻苦的工作以及对自然的实验性研究。另一个吊诡之处是,人们对牛顿之伟大的世俗性描述,又带有传统宗教崇拜的鲜明特征。在讲座之后的问答环节,与会学者跟艾利夫教授就天才的概念、想象力的定义等话题进行了具体而深入的探讨。
本次讲座为“清华科史哲讲座”第一讲,“清华科史哲讲座”是清华科学史系长期设立的系列学术前沿讲座。
牛顿的理性宗教(The Rational Religion of Isaac Newton,自然科学史研究所,9月22日,主持:韩琦研究员)。自十八世纪以来,一种关于牛顿的“启蒙主义”观点逐渐流行开来,那就是牛顿到了晚年才开始沉迷于宗教和神学。这是启蒙思想家为了调和牛顿的两种形象——理性的奠基者和痴迷的神学家而想出的折中办法。二十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大量牛顿神学手稿的披露,人们逐渐了解到牛顿不仅从小笃信基督教,而且年青时就已开始研究神学。不管我们今天如何看待牛顿的宗教信仰,牛顿自己认为他的宗教研究是完全“理性的”。虽然科学有科学的探究方法,宗教有宗教的研究路数,但是两者都是理性的。无论在哪个研究领域,牛顿都非常警惕偏见、臆测和过于依赖人的权威所带来的危险。牛顿笃信“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因此人被赋予了足够的理解力;只要借助理性和适当的方法,人是能够理解《圣经》的。在宗教研究上,牛顿提倡理性,反对神秘主义。他相信基督教是一个理性的信仰,不幸的是后来被掺入了一些不可理解的内容(例如三位一体和道成肉身教义),或者被牧师们作了不可理喻的阐释。牛顿认为自己的使命,就在于通过研究早期教会史来揭露罗马教会是如何与魔鬼合谋来腐蚀基督教的纯正教义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牛顿用来理解《圣经》和研究教会史的方法,后来则成了启蒙思想家攻击各种形式的宗教的利器。
3 牛顿研究前沿座谈会以及《科学文化》第二次编委会
9月18日,艾利夫教授参加了袁江洋教授召集的“牛顿研究前沿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还包括鲁大龙、郝刘祥、刘孝廷、赵振江、苏湛、柯遵科、万兆元等相关领域的学者以及国科大和自然科学史所的部分研究生。与会者围绕牛顿的光学、炼金术、形而上学、宗教和政治思想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学术探讨和交流。
中文版《牛顿文集》仍是讨论的一个热点。许多近代著名科学家都有全集出版,但是被视为近代最伟大科学家的牛顿却迟迟没有全集问世。这一方面是因为牛顿有关神学和炼金术的“非科学”手稿长期以来被视为不适合或不值得发表,另一方面也因为牛顿未公开的手稿太过庞杂(约1000万余词),编辑和出版的难度非常之大。近20年来,“牛顿项目”一直致力于在线出版《牛顿全集》,成绩斐然,这为将来印刷出版《牛顿全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自牛顿以“奈端”之名侧身《历象考成后编》以来,牛顿进入中国已有270年的历史了。在此期间,牛顿的科学发现被慢慢介绍进来,但牛顿著作译成中文的为数甚少。与会者一致认为,这一“短缺”现状与牛顿的著作数量及巨大影响不符,与中国学者和读者的期待不符,与中国的国际学术地位和发展方向不符。尽管英文版《牛顿全集》尚未问世,中国学者应该可以先行一步,为中国读者选编并翻译一套高质量的《牛顿文集》。与会者再次提议,以中英双方学者合作的形式,适时启动“《牛顿文集》的编辑、中译与出版”项目。项目的基本思路是:(1)《牛顿文集》的选编工作要以国际牛顿研究为基础;(2)选编不求全求大,但要将最能体现牛顿思想、工作与成就的著作与文稿收录在内;(3)中文译本既要准确,又要可读性强,并要体现出较高的学术质量。为此,应该筹备成立外方专家委员会和中方编译委员会:前者主要提供选编建议和翻译咨询,后者负责确定编辑方案并实施翻译工作。两个委员会除了平时保持密切联系之外,还应经常开展相关主题的研讨活动,进而把项目变成一个集翻译和研究为一体的进程。作为预热,与会者建议不妨先将两本最新的牛顿研究著作——艾利夫教授主编的《剑桥牛顿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Newton,第二版,2016)
及其新著《大自然的祭司:牛顿的宗教世界》(Priest of Nature: The Religious Worlds of Isaac Newton, Oxford,2017)——译成中文,并初步讨论了译者的人选。刘孝廷教授补充说,实际上《剑桥牛顿指南》的翻译工作已经开始了,只不过依据的是第一版;现在第二版已经出版,当然应该以第二版为原文本。
9月16-17日,艾利夫教授还作为编委会成员参加了在京举行的“关于科学文化及公众常识研讨会暨《科学文化(英文)》期刊第二次编委会”。《科学文化》是中国科协主管、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NAIS)正在创办的一份新的英文期刊,旨在“刊登国内外科学文化发展趋势和最新动向,推介中国科学文化建设和实践的研究成果,构建科学文化学术研究的国际交流平台”。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期刊选题及组稿工作,讨论重点为科学文化和公众常识在不同社会语境下的内涵界定。
作为该刊的国际编委,艾利夫教授作了题为“科学史上的重要主题”的发言,列举了科学史可资当代科学文化探讨的九个主题。(1)全球科学史视角:有关科学技术史的讨论,大都是以西方为中心的。西方之外,是否还有别的研究视角?在何种意义上科学是全球性的?(2)危机与环境:不同国家的人们在历史上是如何获知有关危机的信息的,特别是有关污染等环境危机的信息的?对于发现的危机,不同国家的人们采取了怎样的应对办法?公民拥有哪些应对危机的权力和途径?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环保危机方面,中国拥有丰富的经验,可通过这份刊物与世界分享。(3)公众对专家的信任或怀疑:科学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分野,并非那么泾渭分明,而是互有渗透。今天的公民有自己的场所和空间来表达对科学结果的不同意见,乃至反驳专家的知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西方公众会习惯性地怀疑专家,认为专家大都有其私心,并不能做到公正无私。(4)作为一项独特人类活动的科学:在什么程度上,科学可以像其他人类活动一样被人类研究?又在什么程度上,科学与其他人类活动有所不同?因何不同?科学无疑是进步的典范,但是科学的进步又该如何理解和解读?(5)科学的意识形态神话:这里涉及人们或公开或私下讨论科学的方式,以及对工匠作品、集体工作或杰出个人的呈现与解读。例如,科学进步是集体的功劳,还是“英雄人物”的成就,抑或只是西方的特权?(6)科学与价值观:西方世界对科学与价值的区分,涉及科学与宗教、科学与伦理等议题,例如发明治疗癌症、延长寿命的技能所涉及的价值观,利用动物进行实验所涉及的道德伦理,等等。(7)技术进步的社会影响: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进步对人们的工作条件、生活质量、两性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不久的将来还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历史又会告诉我们,这样的进步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好处或者危险?(8)审计社会:科技价值观(诸如资助标准、评价体系等)是如何在西方以及非西方社会中发展起来的?STEM(科学、科技、工程和数学)教育价值观是如何衍生出官僚文化的?对一个国家而言,成功培养本国科学家和工程师在何种程度上是一个成功国家的必要前提?(9)对话与文献共享:共享期刊会刺激对话,可向世界传达中国科技的进步和成功,促进西方对中国乃至俄国和印度等国家的了解。就此而言,《科学文化》应有更为广阔的国际视野;如果可能,希望能够以中英双语出版。
短短两周期间,艾利夫教授日程安排得非常紧凑,先后在国科大和其他高校及科研单位做了十二场讲座,并参加了一次座谈会和一次编委会。通过这些活动,他得以与国内科学史学者进行接触和互动,巩固并拓展了中英科学史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与联系,为中国的科学史研究特别是牛顿研究注入了新动力。
(兰州交通大学 万兆元)